
 Qzone
Qzone
 微博
微博
 微信
微信


马路
39年前,马路从新表现主义绘画起步,后又渐渐远离。10年前,有朋友让他参加抽象艺术团体,他婉拒,说自己的绘画不抽象。5年前,马路参加“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展,有人说,抽象画非要参加具象展,但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具象。有朋友出主意说,你说不出来是什么,你可以说不是什么。但当他真的说了一大堆不是什么后,却又招来别人的疑问:你说你的作品不抽象、不具象、不表现,那到底是什么?
给艺术风格起名字,是为了便于交流,但当现有的词汇不能准确表达自己艺术思想的时候,怎么办?这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原造型学院院长、油画系主任马路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4月3日,“‘无’中生‘有’——马路炁象作品展”在西安崔振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马路2010年以来创作的炁象作品100余件。这些既不同于西方经典的抽象,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意象的作品,再次引发了理论界和艺术同道的关注与讨论。
其实,马路成批的“炁象”作品,最早亮相于2020年“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年度提名”展。作为央美标杆性的展览,“提名展”素因其严格的遴选标准和参展艺术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闻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参展艺术家所在领域艺术发展的新趋势。当时,“提名展”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理论出版部主任红梅在认真梳理了马路的创作后发现,他近10年的艺术探索与思想轨迹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抽象艺术本质的关注;转向思考自己的艺术与抽象艺术之间的区别;进而将创作过程的自然性与绘画本质的自然性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了新的艺术价值观。
于是,红梅说:“你的作品既不抽象,又不具象,那展览就叫‘无象’吧?”
马路说:“把‘无’字下面加四个点吧,叫‘炁象’。”

炁象,2011—2020年,180×210厘米,丙烯、色粉,综合技法马路
炁,读“气”声,有气象的意思。“无”下面加了四个点,如火焰在加热,是表达一种能量。“马路用‘炁象’来指称自己十余年的艺术,从而与抽象艺术和意象绘画等艺术形式区分开来。他将整个世界视为是各种不同的能量形式彼此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描绘的是由时刻变动的能量所形成的各种不固定形态,因此并不抽象也不是意象,而是一种一直客观存在却未被注意的形象领域。从一定程度来看,这种不固定的形态又是自然、人生恒定变化的某种视觉显现。”红梅说。
例如在作品《炁象》背后的题记中,马路这样记录下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这是一幅画了十年的作品,今天方能告一段落。因为人总是在生活中认识,自在变化中。各种力的作用,使作品也在发展,只是容下的更多。人生无常,正是其诗意之所在。学会欣赏无常,才是正常。所谓审美,自是认识之根本。多方交错,故更名为炁象 。放下具象之得失,来到更高处,看宏观、 微观于一体,方得自由自在。远离于深入中,静观及细查。放下自己,才活出自我。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冬天画暑日,2017年,210×180厘米,丙烯,综合技法马路
在许多人看来,马路所呈现的融汇中西、入古出新的艺术面貌,与他个人开阔的文化胸襟以及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自信有着极大关系。
马路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82年考取公费研究生,就读于德国汉堡造型艺术学院自由艺术系,属于改革开放后钻研“德系”艺术最早的青年画家之一。在德期间,马路受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影响,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我对德国艺术最初的认知,仅限于鲁迅先生早期介绍的德国木刻。但真正到了德国之后,写实的、抽象的、装置的、电子互动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视野。德国艺术的色彩、造型,以及与时代、历史、民族性的关系等,也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当时,我发现唯一一个与中国文化相通的是新表现主义,它很像中国的写意画,但又不是。新表现主义特别重要的观点是以个人来书写整个民族的神话和历史,这就让我联想到中国画的笔墨。” 在马路看来,艺术学习和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在于发现,正如中国书法所追求的古意也是古人的发现一样,今人也应该在自然中发现新的现象和形式,而不是一味地照搬模仿。德国的学习之行,也为马路之后的艺术探索埋下了求变的种子。

泛水约风,2017—2020年,90×130厘米,丙烯,综合技法马路
1984年回国后,马路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在当时极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马路艺术探索的锋芒初见犀利,在造型个性和表现语言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认识,也在题材、媒介、技巧上拓宽了路径。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对绘画的坚守成为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普遍难题。马路思想上的敏锐使他转向探索艺术图像的纯粹精神价值,从表现性语言领域向抽象性语言世界迈进,也通过吸收中国艺术的“写意”传统,逐渐模糊甚至消解了具像的痕迹,回到绘画本身,并将感受性与意象性形式化,构成了宽阔、深邃而充满生命力的艺术表达。可以说,马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语境中找到了中国艺术新的生发点,也找到了自己艺术创新的原点。尤其近年来,马路在绘画上的探索更是形成了不少新技法,乃至属于他的“特技”,这也使得他的绘画语言足以与新媒体、装置、影像抑或其他视觉表达相抗衡,充满魅力。

那霭,2010年,18×210厘米,丙烯,综合技法马路
“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艺术家求索创新的重要代表,马路对西方和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与特征有着深度的判断,也始终在文化语境不断变化的情形中保持着清晰的艺术认知和文化意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中国长期以来处于西方文化输入的被动局面,这也使得中国与世界在艺术的交流上存在逆差,因此,艺术家们需要坚持并继续探索中国话语体系下的文化自觉,要在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上有更大的创新性和共识度,才能更为从容地应对全球艺术的趋势和现状。“对于马路来说,他正是将美术创作和反映社会现实、彰显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民族的人文传统和艺术传统中走向了当代创造。他艺术中呈现的‘象’,正是当代中国全面发展的蓬勃气象的视觉反映。这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范迪安说。

默与天言之二,2015年,180×210厘米,综合技法马路

余纯信的最后,2015年,140×210厘米,综合技法马路

红绿,2017年,130×90厘米,丙烯,综合技法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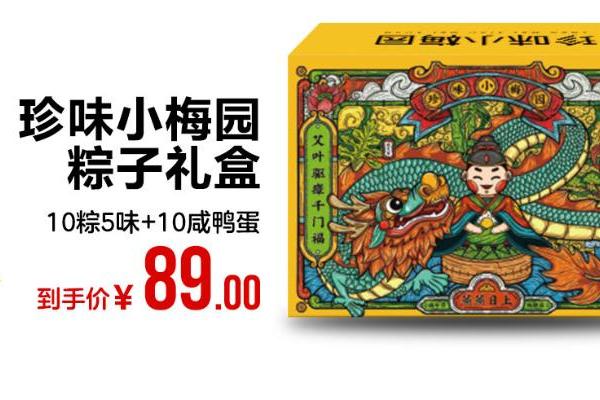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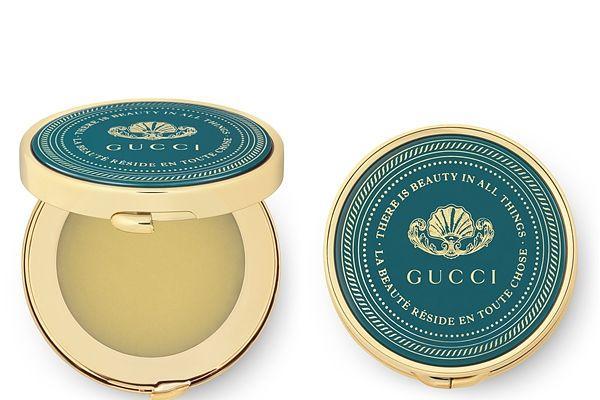
TOM2022-06-07 10:3306-07 10:33

盖世汽车网2022-06-07 10:3106-07 10:31

TOM2022-06-07 10:2506-07 10:25

TOM2022-06-07 10:2506-07 10:25

TOM2022-06-07 10:2406-07 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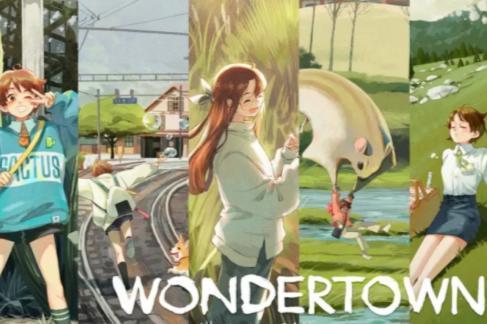
TOM2022-06-07 10:2406-07 10:24

TOM2022-06-07 10:2406-07 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