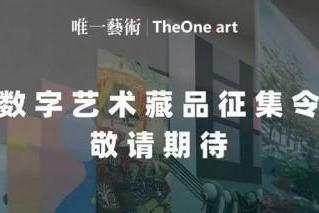Qzone
Qzone
 微博
微博
 微信
微信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千百年来她有时和缓温驯犹如慈母的臂弯怀抱,有时不羁冲决如同严父的训导呵斥,慈母严父共同培育出的黄河两岸儿女坚忍不拔的精神特质,也催生了一个个自强不息的“黄河故事”。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广大作家、艺术家“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黄河进入山东,哺育了齐鲁儿女,润泽了山东大地,却也因频繁改道、泛滥,使下游滩区群众饱受水患之苦,田地被淹、家园被毁伴随着许多滩区人的成长记忆,而搬出“水窝子”、安居乐业,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滩区人的梦想,这一多年的梦想随着山东黄河滩区迁建工程的实施而得以实现。这一壮举及其前后发生的故事,演绎了壮美诗篇,需要我们用艺术加以呈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黄河与脱贫结合这一炙手可热的题材,一时吸引很多院团和剧作家的关注,但热闹一番后,很多人却对这一题材望而却步。因为寻找到独特的切入视角,既讲好脱贫故事,又要讲好黄河故事,使之从众多脱贫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不忘初心、勇挑重担,创作推出了山东梆子《梦圆黄河滩》,以过去四十年黄河滩区的变迁为背景,通过一位滩区汉子的视角讲述黄河滩区老百姓遭受水患之苦,最终在新时代党的关怀下搬上村台安居梦圆的感人故事,用全新的舞台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段表现出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内涵,视角独特而新颖,人物饱满而典型,剧种风格鲜明而突出,艺术地书写了“黄河滩区脱贫大迁建”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画卷。
该剧的成功离不开主创作们扎根泥土、脚踩大地,离不开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和真情感悟。“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戏剧创作特别是现代戏创作的先决条件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山东梆子《梦圆黄河滩》的创作过程中,两位年轻的编剧多次深入黄河滩区进行采风,既倾听了滩区人民对苦日子的回忆,更多感受到的是滩区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感受到了黄河的厚重、老百姓对黄河“爱恨交加”的情感、搬入新家面对新生活的激动、难题面前勇于担当的气魄。脚踩大地才能放飞想象的翅膀,经过深入采风、思考,两位编剧找准了最佳切入点,把深埋在黄河滩区里的那些鲜为人知、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东西给挖掘了出来!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开掘方式,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脱贫故事,描摹出了黄河滩区人民的种种际遇、命运变迁和观念转变。
该剧另一特色是题材与剧种的完美结合。山东是戏曲剧种大省,不同剧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齐鲁戏曲百花园,这其中又以山东梆子最为激昂高亢、热情豪放。《梦圆黄河滩》就抓住了山东梆子的剧种特色进行创作,特别是在其唱腔特色上下足了功夫。剧中主角的演唱魅力尽显,不管是高亢明亮,还是刚劲有力,抑或是凄苦悲悯、感时伤怀,都能以声情并茂、韵味无穷的唱腔实现了剧种美学、剧目风格、剧中人物性格的完美统一,生动地塑造黄河滩区人民群像。
该剧最能打动观众、深入人心的是剧中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剧作的灵魂,记录历史进程,讲述时代故事,传递情感、感染观众都依靠他们。当下许多现实题材剧作,特别是英模戏、扶贫戏之所以吸引不了观众,与这些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套路化有很大关系。没有立体的人物作为载体,不管记述的事情多宏大,不管反思和思考多么深刻,不管唱词多么优美,都不能视作一部成功的剧作。英国近代戏曲理论家威廉·阿契尔在《剧作法》中提到:“有生命的剧本和没有生命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着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着人物。”在扶贫题材的戏曲创作中,要把人物写活,其关键并不在于编写的情节是多么的曲折和传奇,而在于将戏剧性冲突融入具体的人物行动逻辑,在人与自我、与他人、与时代的多重关系中,赋予扶贫主题以深刻的内涵。不同于同类题材剧目,山东梆子《梦圆黄河滩》主人公龙长河不是下派扶贫干部、也不是简单贫困户,这一形象改变了凸显扶贫干部的“公式化”创作。龙长河是地地道道的黄河滩区汉子,他一生在追求安居梦,为了这个梦,他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庭。该剧充分挖掘了他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满足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永恒追求,激发他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唤起观众对脱贫攻坚事业的认同与支持。
我们承认,当前的舞台艺术创作,不管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是表现当下的真人真事或讴歌先进人物的作品,在对作品现实意义的深层挖掘和哲理思想的探寻方面,都存在程度不等的缺失。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要想从整体上去理解她,用全部的心灵情感去体验她,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她,更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山东梆子《梦圆黄河滩》在描写黄河滩区迁建这一历史画卷的过程中,没有简单的图解政策,而是试图用现代意识观照传统思想,试图通过一个黄河滩区农民汉子的悲欢离合,使脱贫故事脱离表层和概念,赋予剧目以反思和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和观众形成交锋交融,在精神上和观众进行对话,这是该剧特有的气质,也是剧目的初衷和追求。